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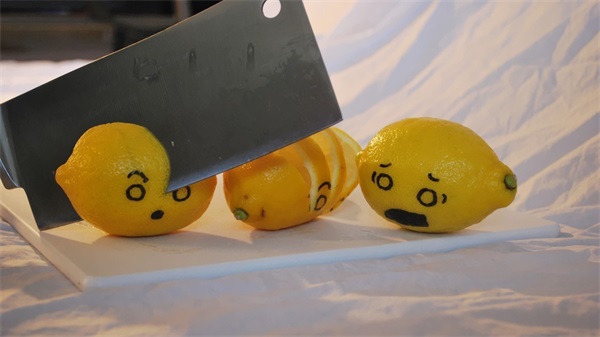
马庆民
夏日里,走进农家小院,最打眼的要数那一排排黄瓜架。一片片深绿色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泽,一个个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垂挂在柳条棍上,在和爽的夏风里摇曳生姿,惹人怜爱,俨然成为了乡村里一道绝美的风景。
菜有好多种,黄瓜来当家。黄瓜,在乡下是最司空见惯的物种,既可以当蔬菜下饭,又可以当水果解馋。所以各家不管院子大小,都会留出一点空地种几垄黄瓜。
我家的小院也不例外,母亲常在院子里种黄瓜,瓜苗过膝时便忙着搭起了木架。它们也很争气,总是长势喜人。很快,苗儿蔓了秧、吐了须,爬上了篱架,结上了黄艳艳的花朵。待小花渐渐地失去了光泽,谢落之后,就绽露出一只只毛茸茸的小瓜。不久,一根根饱满丰实翡翠般,水灵灵的黄瓜挂满了黄瓜架,坠得藤蔓都快断了。
小时候,我常纳闷,明明黄瓜全身都是绿色的,为什么非叫它黄瓜。后来,看见黄瓜架上挂的老黄瓜,才似懂非懂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读的书多了,才得知我似懂非懂的结论是错误的。
原来黄瓜并非我国原生物种,它原名“胡瓜”,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将此带回中原,广泛种植于大江南北。胡瓜更名为黄瓜,始于十六国时期的后赵,这里面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。后赵王朝的建立者是石勒,他是羯族人,因为自己是胡人,很忌讳人家说“胡”字。有一次,石勒召见地方官员,其中有个郡守叫樊坦的很机灵,御赐午膳时,石勒指着宴席上一盘碧绿的胡瓜,问樊坦:“卿知此物何名?”樊坦脑瓜儿一转,计上心来,恭敬地回答:“紫案佳肴,银杯绿茶,金樽甘露,玉盘黄瓜。”石勒听后,龙颜大悦,赦樊坦无罪。自此,胡瓜便成了黄瓜,在民间流传、沿用至今。
黄瓜是夏日乡间的小清新,细溜溜的身条,顶花带刺,咬一口,微甘爽脆;再咬一口,暑热顿消。又因性味甘凉,入脾、胃,具除热、利水、解毒之功,可疗治烦渴、咽喉肿痛、火烫伤等症,亦有减肥瘦身、美容养颜之效,可谓夏日里的时令菜、平民菜。
黄瓜吃法很多,可炒可烹,可烧可煲,可盐渍可醋泡,皆风脆爽口,美人齿颊。与小葱合腌称之为黄瓜腌葱,葱辣瓜脆,满口生香;切丁与苏子叶辣椒合腌,开胃、下饭一举两得。咸菜丁,黄瓜丁,辣椒丁合拌,谓之穷三丁,永吃不腻。或者干脆啥也不配,刀拍了,点上蒜泥香油一撮盐,拍黄瓜下酒,总吃总有。
乡下老家则更直截了当,摘下黄瓜,清水里洗濯后,咔嚓咔嚓大嚼起来,甘甜、爽脆,解渴,舒惬。
到了城里,黄瓜的吃法也稍富贵了点,如烤鸭、烤肉配以黄瓜条,木樨肉俏以瓜片;溜肉片使得上,凉粉、面缺不得;炒饼能放,汤面里不缺……
但令我印象最深的,要数汪曾祺老爷子的扦瓜皮:较嫩的黄瓜切成寸段,用水果刀旋成薄条,如带,成卷。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,酱油、糖、花椒、大料、桂皮、胡椒、干红辣椒、味精、料酒调匀。将扦好的瓜皮投入料汁,不时以筷子翻动,使瓜皮沾透料汁,腌约一小时,取出瓜皮装盘。先装中心,然后以瓜皮面朝外,层层码好,如一小馒头,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。扦瓜皮极脆,嚼之有声,诸味均透,仍有瓜香。光读起来已然令人满口生津,
“白苣黄瓜上市稀,盘中顿觉有光辉”。黄瓜虽不是菜中主角,也不是果中头牌,却进得了大排档,也上得了国宴。做人,当如黄瓜,富也富得,贱也贱得,随遇而安,安生立命,甚好!
